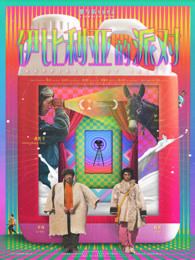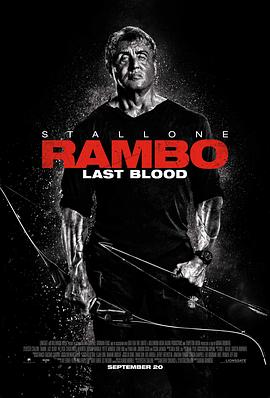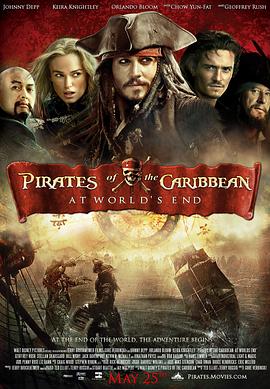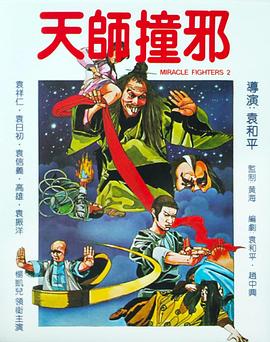剧情介绍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式,艺术总监马克·穆勒还在隔离中,他用视频和观众对话。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图)
平遥相信眼泪。贾樟柯在电影宫哭的那晚,掌声由远及近响起。“这个门厅,我站在这很有感触,我经常下午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那个路口,因为那里挂着费穆先生的像……”贾樟柯说到这里,哽咽停住。
这是2020年10月19日晚上的平遥电影宫。晋北的寒风通过太原孔道,已经吹到了晋中盆地。前一天晚上,贾樟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后的命运。他与他的团队一手扶植了四年的电影展,今后要转交给当地政府。“今年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最后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从平遥古城的仪凤门进去,沿西大街向东走一段短短的路程,就到了平遥电影宫。平遥电影宫是为电影展而设计的。中国的绝大部分电影节(展),在活动场地上都附着于城市原有的商业电影院、酒店,世界上很多电影节也是这样。但平遥不一样。从一开始,贾樟柯就深度参与了将平遥柴油机厂改造为电影宫的整个过程,他将多年参与国际电影节的经验融入到了平遥电影宫的设计之中。
电影宫是一个自成天地的为电影展而服务的建筑。展映、论坛、休憩,各区域的建筑连绵排列,电影人、媒体和影迷在物理空间上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刺激了更高的观影密度和更加鲜活的话语生产。没有一个喜欢电影的人能拒绝这样的捆绑。四五年来,贾樟柯将这里打造成了真正的电影宫殿。
但如果没有每年令人眼前一亮的好电影,电影宫便只是一座黯淡的死屋。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忧平遥影展的未来。没有了贾樟柯,国内最新的好电影肯来平遥吗?没有马可·穆勒,那么多在威尼斯展映的外国电影会来平遥吗?没有吴觉人,青年导演的创投和wip(work in progress的缩写,此处指发展中电影计划)还会选择平遥吗?
2020年10月19日凌晨,平遥电影宫门厅。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图)
唯独缺了贾樟柯
“藏龙的意思就是把龙标藏起来吧。”影评人阿格说,她掏出了口袋里的一个钢印状的小摆件,上面雕刻着龙标的图案。“吴觉人遇到还没有拿到‘龙标’的导演,就会悄悄塞给他们一个这个。”她说。
平遥十日,除了10月18日晚上石破天惊的新闻发布会群访,贾樟柯没有接受媒体的专访。时尚媒体的拍摄请求也被他拒绝。“他看起来很封闭。”一家时尚媒体的编辑10月16日晚上对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平遥人像的专题,几乎拍遍了来到平遥的所有电影人,唯独缺了贾樟柯。贾樟柯把自己藏在房间里,接电话和打电话,但不见人。“他要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协调沟通,消防、防疫……各种工作。”一位接近贾樟柯的影展工作人员对我说。
电影《不止不休》剧照。 (资料图/图)
“龙标”的问题很可能是他们在背后角力的焦点之一。四部入围“藏龙”单元的国产片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拿到龙标,它们在影展的日程手册上被标注为“藏龙abcd”——《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裂流》《汉南夏日》《不止不休》。它们到底会出现在内部放映、媒体场、还是加场公众放映,是这届电影展的悬念。电影展主办方给了《不止不休》最高级别的“防护”,只有内部放映,没有媒体场,更没有公众放映。10月14日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抱怨之声四起。《不止不休》的导演王晶获得最佳导演之后的感言,现在看来是对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的某种提前的宽慰——他提醒观众不要苛责影展方的安排,他们的难处你可能想象不到。
评审团将除了表演奖以外的所有国产片大奖都给了这四部影片。10月16日颁奖的晚上,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兴奋和失落,都只关乎电影本身。但发布获奖名单的平遥影展官方微信号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资料图/图)
派对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那些小瑕疵看成是某种预兆——影展手册迟迟印不出来,影展的每日行程要到前一天深夜才公布,不停地宣传这是一届没花政府一分钱的影展……
开幕片是用快手视频集锦而成的电影《烟火人间》,观众在露天放映的寒风中迅速苦笑退场,并像往常一样一边摇头一边戏谑吐槽。平遥的“电影派对”在口水与嘈杂声中开场。
首先承接媒体口水的入围电影是《伊比利亚的派对》,它的做作与幼稚让人感到震惊,随即是一阵好奇。豆瓣上如潮的恶评没有阻挡导演的表达欲,在很多采访中他侃侃而谈,令人对其坚强的心理防线佩服不已。电影展就是在这种稍显嬉笑荒诞的氛围中开始的。
那时候电影宫的门厅还没有见证贾樟柯的眼泪,却见证了很多派对。好多个晚上,酒会过后,年轻的电影人会在迪斯科音乐中起舞。贾樟柯电影里曾用过的配乐、入围电影里的配乐,都会在舞池中响起,人们即兴地扭动深夜的肢体,像在电影中那样。
张大磊的《蓝色列车》里引用了多首苏联音乐,“它丰富了我们迪斯科的曲库。”吴觉人开玩笑说。但高潮总是属于《go west》,有时候这首音乐响起,赵涛就会出现在舞池中央。比如10月14日凌晨,很多人拿手机拍下了赵涛、张译和廖凡的舞姿,像是《山河故人》与《江湖儿女》在某一个瞬间的相互穿越。
10月18日的变故之后,门厅的舞池寥落了下来。很多人在前几天已经离开,留下的人瘫落在沙发上刷手机,看最新的新闻评论。赵涛没有跳舞,她带着几个女伴穿过舞池,朝室外走去。那晚的主角是一个连续四年都来平遥观影的影迷,她是一个占星师,看《小城之春》的同时会算田壮壮的星盘。她在舞池的边缘使劲地扭动身体,没有人和她共舞,“就算这样,我明年还会来。”她说。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资料图/图)
妈妈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拿了“藏龙”单元最高奖。某青年导演是这一届的“青年评审荣誉”单元的评委之一,影展刚刚过半,他就悄悄对我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部片子。评委会内部的意见也有分歧,支持“妈妈”的人与支持《裂流》的人分成两派,意见难以一致。
“平遥电影节渐入佳境。”“妈妈”首映的那天,一个影评人在朋友圈里兴奋地说道。“或者可以把‘渐’字去掉。”他补充道。经过开局的低潮,影展在中段奇峰崛起,观众特别喜爱的《我们的四重奏》、评委和影评人盛赞的“妈妈”、剑走偏锋的《裂流》和《野马分鬃》接连首映,令人应接不暇。
平遥又一次珍视了创作者的眼泪。“妈妈”的故事是导演李冬梅对母亲的回忆和纪念。她的母亲生育了多个女儿,但还是为了要一个儿子而不停地怀孕。在她初中时,母亲难产而死。这一少年的阴影伴随了她几十年。电影是她对自己生命的印证,也是她试图跨过这道阴影的通道。
对“妈妈”的质疑主要来自它的镜头语言。很多人不能确定这种固定长镜头的安排是否是一种省力的取巧,而对它的解读是否是影评人的自作多情。但是李冬梅用长镜头内部精准的调度和饱满的情绪积累,反击了这些质疑。她的长镜头并不是装模作样或无的放矢,而是通过丰富的自然主义戏剧性和对时间的精确追踪,层层递进地将情绪推向高潮。换句话说,李冬梅的回忆与情绪,非使用这样的镜头不可。这也是本届影展在艺术观念上执行得最为彻底的电影,如果没有内心强烈的情感作为支撑,很难对影像有这样决绝的态度。
“我31岁去澳大利亚学电影之前,看过的电影不超过五十部。”她对我说。在这一点上,她令人想起阿巴斯。他们都不是影迷作者,但对影像有着天赋的敏感。
电影《裂流》剧照。 (资料图/图)
裂流
裂流,又叫做离岸流,是一种向外海方向快速移动的强劲海流。这些海流隐藏在平静的表层水面之下,速度非常快,经常会将在近海游泳的人快速带离海岸,向外海漂流。如果你企图对抗,很容易因体力耗尽而溺水。
余华的水性很好,在海里遇到裂流,他会选择放弃挣扎,任其将他带离海岸,漂向远方。有一次,裂流将他带到了五十多公里外的地方,这是他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面讲的故事。
“生活里也有裂流。”《裂流》的导演杨平道说。《裂流》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平遥将它放在了深夜场,但观众却毫无困意,笑声连连。影片采取了伪纪录、伪业余的影像策略,来描写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电影导演”的粉色糗事——该角色由杨平道自己扮演。观众的观影乐趣很大一部分来自它“伪业余”的拍法,就好比是文玩行业的“做旧”,它的“做旧”技术可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样好玩的是片子本身流露出对“做旧”这件事和中年油腻的自嘲态度。“影像自洽”,这是杨平道在采访时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词,极为有限的成本造成了这样的影像策略,但这种策略却能脱去低成本的桎梏,达到与内容的自洽。
生活的裂流将《汉南夏日》的主人公推得更远。《汉南夏日》是影展的压轴戏,来自武汉的故事充满了水汽的氤氲和少年人的潮湿心境。女导演韩帅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娄烨,但她没有被理论素养束缚,依然能保持镜头里敏锐的生命触觉,颇为难得。塑料模特的一场戏,堪称在当代电影里,继《过春天》里最聪明的床戏后,最聪明的少年情欲戏。
如果要给这届平遥影展一个关键词的话,“裂流”也许是合适的。裂流将我们卷向远方,不知归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平遥这座浮岛也遭遇到了它的裂流。岛上的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但裂流涌动,最终将其带离原有的轨道。掌舵者贾樟柯也许很早就知道它的命运,“从第一届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有着这样的思想准备。”吴觉人说。
电影《汉南夏日》剧照。 (资料图/图)
回归
一种真实的情绪在平遥蔓延,在贾樟柯10月18日的讲话之后。也许在外人看来这种情绪多少有些过度渲染、自我悲情,但它贵在真实,又极为短暂。10月18日之前已经离开的媒体记者、曾经来过平遥的电影人、还留在平遥的志愿者,当晚他们的朋友圈里都弥漫着某种克制的悲伤,似乎大家都达成了某种默契——过度地展示情绪对前途未卜的影展命运并没有太大帮助。
很多人沉默但迅速地订了回平遥的车票。某些媒体记者10月19日一大早从北京回来了,他们10月17日刚刚离开平遥。“我发微信叫(导演)霍猛回来了。”吴觉人说。
纪念品商店里的排队长龙从10月18日晚上排到了19日白天,第四届平遥影展的专属斜挎包被抢购一空;电影宫里可以看到很多人拿着各式设备在拍纪念vlog;程青松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展板大头像面前合影——他们都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留住平遥的最后一刻。
10月19日晚上是最后一场酒会。入夜后平遥古城变得漆黑一片,电影宫门厅的灯光微弱闪烁,像是无边海洋中摇摆不定的浮岛。浮岛上曾有的憧憬与雀跃,已经渐渐被海洋所吞没。今晚没有想象中的last crazy,而像是一次例行公事,把该喝的酒喝完,该跳的舞跳完。
“跳舞的都是不认识的小孩啊。”木卫二说,他是一个成名于21世纪初的影评人,已经不认得新出来的这些“小孩儿”。像其他人一样,他也在揣测背后的真实原因。但是其中讨价还价的细节、反复拉扯的阵痛、各利益方的阵地攻防,当下只能变成当事人的一种“不足与外人道”。
从北京赶回来的记者和我聊着这一整天的采访。在白天,我和他合作抓访了很多留在电影宫里的人,想知道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感受。“你说,是不是平遥特殊的地理原因,才让它的氛围这样独特。”他对比了北京和上海,“上海北京可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一摊聚完,大伙儿自然分散成几个小团体,再聚下一摊”。但平遥不一样,人们被聚集在电影宫,出了电影宫,没地方可去。平遥电影宫的当代文化是平遥古城的单一的古代人文景观的一种变奏、一小片绿洲。
将要落幕的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现场,工作人员正拆除展板和海报。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图)
远方
来自远方的人聚拢在平遥,他们在电影中到达比远方更远的地方。尽管人们嘲笑《伊比利亚的派对》中想象“远方”的糟糕文艺腔,但“远方”不得不成为一个电影展里人们交谈时不言自明的前提、当下的背景,和未来的心之所系。
李冬梅自澳大利亚归来,带着从远方学到的电影回到故乡的山里。张大磊和他的《蓝色列车》,要去很远的波罗的海岸边参加下一个电影节。年轻时候的余华在故乡的海里游泳,但是浙江的海裹挟着长江口的泥沙,亘古以来的泥黄色湮灭了人们对大海的想象力。“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余华在纪录片里说。
一部艺术电影最初的生命,就如这样漂流在地球上。从这一大洲的电影节,到下一大陆的影展,在这个港口它遭遇了嘘声和口水,也许下一个港口的观众会送上鲜花。如果电影节对电影来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电影在游到海水变蓝之前歇脚的地方。它提供补给、安慰,也许还有奖金支撑它继续游下去。很多电影人哀叹平遥的变故,就像是疲累的水手哀叹一座海上补给站的消失。
某一晚的派对上,我听到微醺的占星师给一个人算了星盘,“你适合去很远的地方生活。”她对他说。那个人陷入了沉默。“那个地方很远很远,可能是在海的另一边。”“那里的海水会是蓝的吗?”我心里想。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