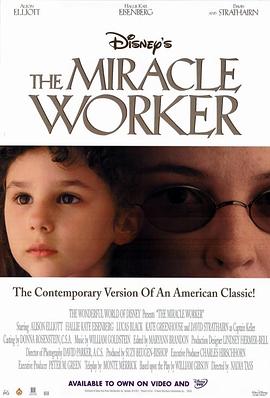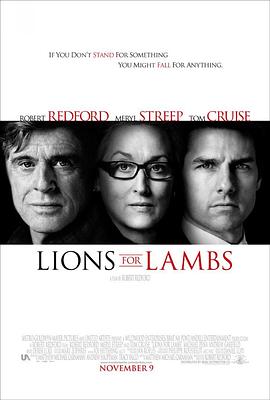剧情介绍
他和他母亲走散了,站在路边的土包上,他努力想记清他母亲的脸,可越想越模糊,越想越恐惧。
记不清是多少天前了,他寡母带他从家乡逃出来。他只知道他家乡叫煤渣子街,再大点的地名一概不知。煤渣子街很窄很直,没有一棵树,起风时,灰尘直从街头飞到街尾的小山上。山上都是坟堆,稀稀疏疏的几块碑,他父亲也葬在山上,小小的黄土坟堆,围了一圈大小不一的石头,没有立碑。他家就在山下,一间三进的房子,因为靠山,屋内虽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总是很阴暗,看不大清人的脸。他母亲长年坐在门口做针线活,所以他每次从外面回家,总先看到他母亲的头顶,头发梳得很顺,纂得很紧。他母亲一听见他回来,总要抬头看他,很高兴的跟他说东说西。但是那仰着的脸于他太过熟悉了,现在想来反而模糊不清。
他家对门是一家小店铺,门前一个大灶,一只大铁锅,臭猪肉熬油,成年弥漫着诱人流涎的煎臭肉香味。他母亲每月到这家店铺买几次油渣吃,算是打牙祭。除此外,桌上一年难得见到几次荤菜,但他母亲总能把菜煮得很合他的胃口,所以他从未觉得他们的生活不好。
煤渣子街外不远有条通往煤矿的大路,拉煤的车马从那里过,总会颠落一些煤块,街上的孩子就常提着竹篮、拿着铁夹去拾煤块。他也常去,并且很喜欢去,因为可以同伙伴在野外到处跑。有次竟跑到煤矿去看挖煤的洞,那洞口开在山腰上,像土地庙有拱的门,洞斜斜的通向地底,又深又黑,两边相对立着没剥皮的撑树,一对比一对暗淡,看不见几对,后面的都隐没在黑暗深处了。他不敢进去,怕洞顶会塌下来,那撑树实在太细太疏。山脚还有个废弃了的洞,光线透进去,可以看到里面已是一片水,横七竖八浮着些不知是什么东西。那次他母亲罕见地生了他的气,因为她到处寻他不着,他每次去拾煤块,她都会估摸着时间去接他,提他拾得的煤块。此后,他再也不敢跑得太远,怕害得她寻。
那天午后,他又去拾煤块。傍晚,太阳还没有下山,他母亲来接他。煤有点多,她提着走了一段,就停下来歇息。他蹦蹦跳跳在前面走了,过豆腐店门口时,见二狗子正端着书在练鬼子话,便说了句汉奸。二狗子也是他的玩伴,有时也去拾煤块,同去拾煤块的也还有几个读书的,他们嘴里不时会蹦出几句鬼子话,没读书的几个就开玩笑骂他们是汉奸。但不知为什么,这次二狗子动了气,扬起书就朝他砸过来。两个很快扭打起来,二狗子虽比他高大,却打他不过,被他骑在身下。开始叉手旁观的二狗子娘立即过来一把把他拉倒在地。他爬起,就骂他们一家子汉奸,并冲向二狗子娘。她又把他甩倒在地。他又爬起冲过去。二狗子娘边对付他,边对围上来的看众说:“大家看看,看看,小孩子哪里会说这话,肯定是大人教的,真正是,这样的大人,这样的大人,养子不教,还不如养个猪。”
他母亲闻声赶来,一面去拉倒在地上的他,一面说:“我养子不教?再怎么不教,也强过你,一把年纪欺负一个小孩子,也配……。”没提防脑后的发髻被二狗子娘一把捞住,牵起她的头上下提顿,嗷嗷的叫:“啊!啊!我叫你养子不教,叫你养子不教,……。”他站起来,就一脚踢过去,但被他母亲推开了,喊了他一声,他就站开了。他母亲偏着头去抓二狗子娘的脸,二狗子娘头后仰,不住后退,一手格伸来的手,一手仍抓住头发不放,用力往下撏,他母亲的脖子都快反过来了。没有抓到对方的脸,他母亲忽然箍住对方的腰,一下子把她裤带给解了,就往下扯她裤子。二狗子娘忙松了手拉住裤子。他母亲立即占了上风,直身薅住二狗子娘的头发,照她原来的样,提顿她的头:“也不去茅厕照照,看看你这鼻子,看看你这眼,也配骂别人是猪。”又把她拖到了二狗子面前,指着二狗子说:“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下的是什么货,眼睛不比鼻孔大,也配做汉奸,说他汉奸,抬举……。”二狗子娘忽然腾出一只手来,给呆站在面前的二狗子扇了一耳光,二狗子哇哇的哭起来,骂她娘的娘。这倒很出乎他母亲的意料,就松开了手。看的人这才过来把她们拉开了,一顿劝,终于各自散了。
夜里,隔壁与他母亲素不相能的他家的远亲吴四娘上门来了,一进门就拉住他寡母的手,软声细语的,要倾耳才能听到。她是来告诉他们母子逃命的,二狗子家准备明天去告官了,大家都说就是他们不告官,官也会知道的,那么多看的,哪能不知道,嘲笑别人学日本话,是要杀头的,二狗子家如果不告官,也会被抓,她吴四娘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他们这些的。 她又是帮着他母亲哭,又是帮着骂二狗子他们一家子。他母亲涕泪满面,说了很多感激与愧疚的话。
后来,她说:“妹啊,不用担心,钥匙给我,房子我帮你看着。”听了这话,他母亲似乎是忽然回味过来了,甩了一把鼻涕,冷笑几声,说吴四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说她又来打他们房子的主意,她大儿子讨婆娘打过一次主意,现在二儿子又要讨婆娘了,又来打主意了,吓他们娘俩,等他们娘俩跑了,好霸占房子。她说她偏不跑,偏要瞪大眼看他们娘仨叠两儿媳妇睡一个冷炕头。说她自己真是瞎了眼,差点给骗,亏了一顿好哭。吴四娘一脸窘态,含糊不清的辩解,说她看在亲戚的份上才来,说她一片好心......,说不为自己,也为孩子……,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杀人的……。
熄灯睡下后,朦朦胧胧听到她母亲又起来了好几次,起初是到水缸舀水喝,后来是翻箱倒柜的声音,再后来是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饭菜的香味在屋内弥漫,梦中恍恍惚惚以为是大年夜了。她母亲把他喊醒时,窗上还是一片黑,他揉着眼睛还想睡,她要他赶快穿衣服,起来吃饭。饭菜都已在桌上,旁边凳子上有个很大的蓝布包袱,他就问他母亲谁来了。她母亲说没谁,要他赶快吃饭。菜碗里是鸡肉,他母亲把家里唯一的鸡杀了。鸡是圈在屋后的,原来有两只,是半年前张大娘家母鸡孵蛋时,他母亲送两枚鸡蛋去搭着孵的,都是母鸡,本指望养着每天下个蛋给他吃,但一只跟在他脚后被他不小心踩伤了,他曾见人把将死的小鸡覆在斗笠下拍拍就活了,他也学着做了,可斗笠快拍破了,也没有救活过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慢慢死了,剩的这只还没下蛋,不过据他母亲说,应该很快就要下了。他问他母亲为什么要把鸡杀了,剩饭剩菜不要它吃了吗?不等它下蛋了吗?他母亲说不等了,快吃吧。等他吃完,他母亲把剩下的饭菜用家里最大的碗装了,压实,倒扣了只稍小点的碗,用帕子包了,扎紧,兜在一个小布袋里。然后,跟平日一样,将桌子收拾干净,碗筷洗干净,筷子放进竹筒里,碗倒扣在桌子上,倒洗碗水。都收拾停当后,她端起灯,在每个房间里转圈,好像在照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拿,又把灯放回桌子上,一手把包袱挎到肩上,一手提小布袋,吹灭灯,还在屋里站了会儿,才拉着他跨出门槛。屋外天才麻麻亮。他母亲将小布袋给他提了,轻轻合上门,仔细锁了,转身要他在前面走。他问他母亲他们去哪里。他母亲说,别问,听娘的,娘叫你往哪走你就往哪走。他们没有走常走的煤渣子街,而是走很少走的坟山脚下的小路。没走出多远,他母亲站住了,留他在原地,独自回走。煤渣子街直直的戳在黑暗里,夜游的东西在这里那里碰出点点声响,没有一点人声。他母亲回到家门前,推了推门,又摸了摸锁,好像想开门,但终于没有开,又转身回来了。
离煤渣子街稍远点,他母亲似乎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碰到岔路口,都很踌躇,有回走出很远了,但越走越荒凉,要走到深山里去了,只得往回走,再走另一条路。后来,再遇到岔路口,他母亲就要他选,说他是小孩子,运气总是好的。他就总是选走大路,因为好走,又可时常遇见人,虽然有时他很不喜欢遇见人,但遇见总比遇不见要好。起初,他们零零星星遇见一些逃难的,后来越来越多,最终汇入了逃难的洪流中。别人都很奇怪他们,以为他们是去走亲戚的,因为他们只携了那么点东西。他母亲并不辨明,只是顺着说,是去走亲戚。但除了他父亲的舅爷爷的孙女吴四娘这个远亲外,父母两方的亲戚他都没有见过,所以特别好奇,就缠着他母亲问,他母亲就叫他别问,前头很快就到了。但一直走到傍晚,似乎还没有走到,只是随着人流走,夜里也随着人流在野外过夜。第二天,他母亲又说,再走一天看,到了住几天就回家。就这样走了一天又一天,有几次似乎要停下来了,但事到临头,他母亲又动摇了,仿佛被人流卷着,停不下来了,越去越远。
这天临近这座城市时,已是午后,城门口挤满了逃难的人和牛马牲口,但城门紧闭。他随他母亲站在人群中,就像站深水中一样,给推来推去,周围浮着一圈比他高的人的脸。他觉到鞋子里有粒沙子,正在脚趾间,但不能弯腰脱鞋将它倒出来,于是他试着用脚趾将它拨到鞋尖里去。就在他专心拨动那粒沙子时,一股巨大的力量猛然裹住他,几乎将他抬起,一直紧紧抓住他手腕的他母亲的手瞬间崩开了,好像绷断一根绳子。他本能地跑起来,跑出很远,懵懵懂懂藏身到城墙边一块巨石下,回身看时,只见人群仿佛一脚踩散的蚂蚁,纷纷不已。人畜声、飞机声一时都响亮起来。他这才意识到她母亲不见了,可又不敢立即去寻找,因为有两只飞机正在低低盘旋,只得用目光四处搜寻,终究不见踪影。飞机终于飞走了,一颗炸弹也没扔。接着就来了军队,又是车,又是马,急急冲向城门,城门洞开,军队鱼贯而入。四散的人群立即像潮水一样,跟在军队后面,涌向城门。他盯着流动的人群,搜寻他母亲,可还是不见踪影,于是他就爬上路边一个最高的土包上,希望他母亲能看见他。
太阳已经下山,灰尘退去,夜色渐渐上来,人群越来越稀,城门洞越来越深。好几次他仿佛听见有人在喊他,然而四下一望,什么也没有。他想,娘不会死了吧?这个想法几乎把他吓哭。他很想去看看路上那些倒毙的人里有没有他母亲,可又怕走开了错过他母亲,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沿途去查看。看了近处几个不像,他就沿着来路前走。远远望见一具,他就像找东西找急了似的,想那应该是了吧,但立即呸起来,“呸、呸,不要是的,千万不要是的。”走近看了一眼,也不像。再往前走,他看见两个比他小点的小孩在吃力的拖一具胖女尸,一人一边,一人抱一条腿,女尸的衣服下摆已经卷起,露出一段鼓鼓的灰腰身,头发散拖在地上,巴满灰尘,像一把脱光谷粒的老稻草尖。他们等他走过后,就松懈了,都把腿放下,各坐在刚才自己抱过的那条腿上,嚯嚯的哭起来。他吓了一跳,回顾了几次,然后就跑起来,越跑越黑,觉得前面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心想他母亲肯定已在城门口等他,于是又往回跑。那两个小孩还坐在那里,只是已经没有哭了,夜色下已看不清他们的脸。他越过他们,直跑到城门口,什么也没看到,疑心他母亲找他不着又去别处找去了,十分懊悔自己不该走开,决定不再走了。又爬到那个土包上,高高的站着,以便他母亲一眼就能看到他。她看到我,会多高兴,他想。于是他就去想像她母亲高兴的样子,可怎么也记不真她的脸了,就很害怕再也找不到他母亲了,虽然后面又想只要看见了,就能认出的,但终不能排遣心中的恐惧。
他站累了,心想坐在这土包上,也是很显眼的,于是就坐下了。坐累了,就想即使躺在土包的斜坡上,自己也是能看到前面有没有人来,于是到斜坡上躺下。墨蓝的天空深得怕人,他仿佛正在高处俯视它,身无所凭依,要落下去了,便立即站起来,不再看那天空,找了个可以依靠的地方坐下。不多久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天已大亮,他母亲还是没有踪影,他决定进城去找。城门没有开,他就沿着城墙根走,边走边吃一个又干又硬的饼。饼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他母亲每弄到吃的,总要包一些给他放在衣兜里,说要是跟她走散了,就在原地不要跑,饿了就吃她放在他衣兜里的食物,她会很快来找他的。她还在他衣服腰间没破的地方做了个补丁,缝了一些钱在里面,说是要是她万一一时没找着他,他也不至于饿着。他不时反头看,犹豫要不要回城门口再等等,转过城墙角,走到另一面城墙下,走出很远,他又跑回到城墙角,攀到一棵树上,远远望了望城门口,没有看到什么,便决心绕城墙一周,看看有没有进城的路。城墙下虽都是乱石和灌木丛,但一条人踩出来的土路或近或远随着城墙,并不难走。再转过一个城墙角,他看到城墙已被人拆出了好几个缺口,于是就从一个墙缺进了城。他想首先得找到原先的城门,娘肯定是被人流卷进城内出不去了,现在肯定在那城门后等开城门,只要找到那里,就能找到她。但城内的路四通八达,他不知道往那里去的路,又不想问人,只好估摸着走,走了很远,忽然想起他只需顺着里面的城墙根回走就行了,不免站住暗暗骂自己傻,立即又往回走。
他来到城门后,城门还没有开,零零星星一些人守在那里,没有他母亲。不远有很多人聚在一座大房子前,举着写有大字的长布,仿佛打着一个个祭幛,有人哭,有人喊,也像是哭丧。房子是建在一个高台上,一道石台阶通向上面,两旁是石栏杆。几个兵挡在台阶口,挡住想挤上台阶的人,每个台阶上也面对面站着两个兵,顶上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哭着嗓子在喊话。他想,要是能站到顶上去,就能看清每张脸,就能看到他母亲有没有在人群里。他从石栏杆翻进台阶,在一侧的兵屁股后贴着栏杆走上去。似乎谁也没在意他。原来那哭嗓子的男人并不是站在最顶上,他身后是块不大的平台,还有好几个台阶才到房子的大门。大门两侧有两根柱子,柱子前有两株模样古怪的矮树。他一手抱柱子,一脚踩到柱础边缘上,倾着身子仔细望下看,人脸在他眼睛里逐一明亮又逐一黯淡。
哭嗓子的男人没喊话了,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年轻人代替了他的位置,一面喜气洋洋的喊话,一面伸手在屁股后抓挠。哭嗓子的男人在旁站了会,就转身走到矮树前擤鼻子,把一条稠鼻涕挂在树枝上,捋了捋树叶,曲着手指用手掌揩鼻子,手掌往上一推,头一抬,就看到了他,皱在额头上的皱纹好一会儿才舒展开来,两手一搓,大步走进屋里去了。
他隐隐有些害怕,想立即逃走,但又想看完再走。
不久,就有两个年轻男子从他身后走到他两侧,把他吓了一跳。他们客客气气的请他下来,要他进屋里去。他们一高一矮,脸都很白,衬得鼻子、嘴格外小巧,都有两条很淡的眉毛,眼睛黑的黑,白的白,比女人还漂亮。 进门后,他们就把他夹在中间,各抓住他一只手,高个抓得有点重,使他稍有点不舒服,矮个却是十分温柔的握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还不住的拨弄他的手指玩,使他一瞬间想起他母亲牵他手的情形,依赖感油然而生,连高个弄得他不舒服也不在意了。
屋内很暗,进门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若有光,两边数不清的门和岔道,门上都有牌子,岔道深不见底。门不时被甩开,人影从一扇门闪进另一扇门里,一片繁忙。脚下哔剥作响,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他很奇怪,眼睛完全适应后,发现地上死满了褐色虫子,一只虫子在眼前飞了一圈,忽然像断了线一样直坠下去。
穿过走廊,接着是一条深深的巷子,一扇门封住尽头,两边是毗连的高大房屋的后墙,没有窗和门户,头上一线灰色的天。进巷子没多远,高个站定,就拔腰间的枪。矮个不慌不忙伸手按住高个拔枪的手,说:“规矩?”“那你说,这次怎样定输赢?”高个边说边将枪插回去。“猜拳。”“好,猜拳就猜拳。”两个都伸出右手拳头,向对方道一声“请”,就开始伸手指变手型,同时嘴里配合着念念有声。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除了听得三呀五呀的,也不大懂他们念的是什么。他们比划了许久,最后都张开了手,高个念的是什么“十”,矮个念的是什么“九”,矮个立刻哈哈大笑起来,高个则涨红了脸,扬着右手,喃喃道:“我这算五个。”原来高个右手只有四个全指头,小指只有一小截。“五个?我还以为是四个半呢,最近真眼花得厉害。”矮个又在鼻子里笑了一声。“我说当五个算。”高个强调。“当五个?”矮个说着,忽然伸手捏了一下高个的半截指头:“那么阿黄当作没吃,这剩的当作是夜饭菜,汪、汪。”高个吓得缩回了手,说:“总不能算我输吧?”“你到阿黄那里去找找。”“找什么?”“找指头,兴许能在狗屎里翻到那半个,凑齐了,算你没输。”高个无奈的笑了笑,凑到矮个跟前问:“你这次想怎么玩?”“玩个坐井观天,……。”便跟高个耳语了几句。“这有什么好玩的?”“当然,比起阿黄大嚼熊掌来算不了什么,输了就得听我的,别废话,走,去废园。”
矮个给他理了理衣领,抻了抻衣摆,牵起他的手在前面走。高个跟在后面。他们打开巷子尽头的门,走进一个荒废的园子里,园内杂树遮天,掩映几处破屋,烂果子味扑鼻而来。高个重重关门的声音惊起一群黑鸟,噼噼啪啪下了一阵果子雨。他正盯看那他不认识的果子,高个从后面窜过来,抓住他的双腋,提起他就往前跑,他还来不及反抗,便已被丢进一口枯井里。幸亏枯井不是很深,又是双足着地,所以并没受伤,只左耳被井口的灌木扫了一下,呼呼的杂声一时留在耳朵里没有消散。井约有两个他那么深,石井壁整齐而光滑,他在里面又跳又攀,但根本不可能爬出来。井外矮个似乎与高个吵起来,矮个低低的不知说了什么,高个大声嚷嚷,仿佛在说,这口哪里不够?那口那么深,摔死了,你玩鸟?但他正慌乱着手脚并用想爬出去,一句也没听真。
后面高个凶愤愤吼:“再怎样强过你家一家婊子,男的女的都是婊子。”吼完似乎就走了。矮个随即出现在井口,见他像只青蛙似的胡蹦乱爬,就叫他不要怕,他马上去找东西拉他上来。不一会儿,矮个找来一根枯枝,伸进井里,可是一拉就断作了两截。矮个又离开井口去找了一遍,回来说实在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东西,他得回去拿根绳子来才行。他就求他赶快去拿。矮个犹犹豫豫,说除非他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坐在井里等,他就去拿。他立即答应了。矮个说这是为他好,因为园内的破屋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医生,最大的癖好就是收集尸体,屋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尸体,从未出娘胎的到七老八十的都有,就是缺一具他这样漂亮小孩子的,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要是发现他在井里,一定不会错过机会的。并说那医生是个很漂亮的男人,原先并不喜欢尸体,后来娶了个漂亮老婆,生了个漂亮儿子。一天,那医生抱着儿子,看着儿子的小脸蛋和小小的手脚,越看越爱,俯下头去不停的亲它们,“这时,一种奇怪的欲望缠着他,他用嘴唇轻轻叼他儿子粉嫩的脸颊,张大嘴贴在他儿子的脸上缓缓的哈气,齿尖轻轻的触碰着他儿子的脸,忽然,牙齿不可抑制的往前顶,然后咬合,他感到恐惧和一种咬着自己的肉一样的刺痛,但并不松口,牙齿发软,狠狠的咬进肉里。可是那些诱人的美都没留在尸体上,虽然他曾用过一切办法想恢复那些美。此后,他就爱上了收集尸体,特别是漂亮的尸体。他给每个尸体化妆,像个艺术家一样细细雕琢,没有比死后还保留着生前之美的尸体更美的了,他一直想找一具像你这样漂亮小孩的尸体,你要是再白胖一点就更好了,最好是在最美的时刻死去,美都凝固在死尸上,永恒的美。”说完,笑着去了。
他虽听不大懂矮个的话,但也知道那医生非常可怕,于是老老实实坐在井里等矮个。井上的云去了一拨又一拨,横伸在井口的一枝灌木时近时远,寂静有如他家背后山上冬天的松涛,在井口流动,偶尔的鸟声、果子坠地声、枯枝断折声落在寂静里,就像水滴滴在平缓的河水里,滴出一圈小小的波纹,又立即消失了。娘摊开一块布,剪刀在布上游来游去,像条鱼,嘴一张一张,剪出一下一下的声音,……他为什么还不来,谁在外面走,他么?不要是那医生,好像不是走路声,他要是不来了呢?他想到他母亲和其他许多事,可什么都想不了长久,都会很快回到自己的处境上来。照在井壁上头的阳光已退到井沿,矮个要再不来天就黑了,他看见一条蛇在杯口粗的死泉眼里探了一下头,又退回去了。他一手抓一块石头,站起身来,立到另一边,死死的盯着泉眼。只要你出来,我就砸死你。幸亏井还算宽敞,足够他施展。可是,许久没有动静,他又疑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也许只是只青蛙,但又想,要是天黑了它再出来,自己就要被它咬死,不能再等矮个了,得赶快想办法出去。原先他也想过,要是矮个不来,他怎么出去。开始他想把井里的石头都垒起来垫脚,但那石头都太小,也太少。双脚跨在井壁上爬出去,相对的井壁距离又太远。后来,他看着伸在井口的灌木枝,打量着最长的那支。那是枝檵木,他认识,他家后山上有,很韧,可以用来捆柴的。他想只要能把它抓下来,就能吊住爬上去。他跳起来试了试,根本不可能够着。又想了许久,就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在一只裤脚里扎了块石头,甩上去将灌木枝缠住拉了下来,就立即吊住爬出了井,连裤子也忘了拿了,但不敢再下井去拿,寻来段长树枝,挑出来穿上,立即在破围墙上找了个缺口翻出园子。
他远远的望着那栋大房子,本想绕开它,但想再到城门口去看看他母亲有没有在,自己又找不到别的路,只得硬着头皮朝它走去。
房前的大坪上已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兵在那里,一个手拿棍子,正把一些纸、布条、木棍挑进一堆火里,火照红了他的脸。他挑起一只鞋子举在面前看了看,又扔进火堆里,转头向另一个兵大声说道:“很好的鞋子,可惜只有一只。”另一个兵提着桶,正向一滩黑色的痕迹撒石灰,大坪上已经有很多滩石灰了。大坪外街道上的行人都躲躲闪闪的往这边张望,匆匆走过。台阶上的两排兵还立在那里。一个女人正从台阶上下来,喝醉了似的,从台阶这头摇摇摆摆走到那头,然后又摇摇摆摆走回这头,把只手勾在台阶上一个兵的脖子上,伛偻着身子,似乎要呕吐。那个兵一动也不动。但女人终究没有吐,又摇摇摆摆往下走,边走边开始剥一只桔子,下到第四级台阶,直接把桔子皮甩到大坪上。这时从石栏杆后窜出一个叫化子,拣起桔子皮就塞进嘴里,嘴巴动了几动,伸直脖子,乌黑的脸上鼓起两个白眼珠子。他惊了一跳,以为是碰到煤渣子街的五傻子了——只有他才会拣人家扔下的桔子皮、苹果心吃。那女人乜了那叫化子一眼,把整个桔子都扔了。桔子在坪上滚,那叫化子立即弓着腰象追一只小鸡一样追过去。他刚抓住桔子,第一级台阶的两个兵已经站在他两边了,他们抓住他的腋窝,拖着就把他扔出了大坪,桔子从他手里飞出了老远,他还没完全站起来又向桔子冲过去,拣到后回头冲着大坪这边笑。
台阶上又走下三个人,他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对着树擤鼻子的男人,立即紧张起来。那个男人走到一半就站住了,似乎在环视整个大坪。他觉得那男人的目光扫到他时停留了一下,于是立即拔腿就跑,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追,跑掉了一只鞋,也没敢回去拣。跑出不知多远,他觉得不会有人追来了,就停下来,把剩的那只鞋脱下丢了,看四周都是陌生的,已辨不清城门口所在的方向,只得估摸着乱走。天渐渐黑了,前面的灯光下,有个卖吃食的摊子,热气腾腾。他想起他母亲缝在补丁里的钱,扯起衣服一看,发现补丁已经决开,钱也不见了。大概是在那园子里被挂开的,他想起自己穿过灌木丛去翻围墙时,几次被荆棘挂住,都是用蛮力摆脱的,手臂上被拉出几道血痕,现在还火辣辣的痛。他摸了摸肚子,饿得都快贴着背脊了,赤着踩在地上的脚也冷起来。去讨点吃的吗?他立即想起他母亲在路上跟人谈天说的“讨?多贱哪,还不如去偷去抢。”不能去讨,去偷去抢他又不敢,只好从摊子前匆匆走过,心想要是能在路上拣到几个钱,该多好。在夜里走了很久,从一条街穿到另一条街,从一道巷子走进另一道巷子,有时已经望见城门上的城楼,可始终绕不拢去,所有的路似乎都扭结在一起,再也走不出去,越来越后悔当初不该那么慌不择路,也许根本就没有人来追,也根本没看见他。他不想再在黑夜里走,决计等天亮再说,在一处能望见城楼的屋墙脚下,躺了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被人推醒时,他正梦见自己站在深水中央的一个滑溜溜石头上,不知怎么出去,双脚冰冷,很快就要滑到水中去了。他坐起来,看见一个男人歪在他面前,双手端着一张有图有字的白纸,拦住了半截脸,只露出两个一上一下的眼睛对着他。一会儿后,那男人把纸收起来,他才看清他的脸。他的脸活像一个两头尖的陀螺,只是多了鼻子、眼睛和几道皱纹,一个翻嘴唇的大嘴巴,大得几乎越出了他的脸。他说:“小老弟,你好不要命,还在这里睡大觉,你看看——”他又把他开始端着的那张纸展开,刚想说话,发现有字有图的一面是对着自己的,于是翻转去对着他。“这不是你么,你认得字么?不识字……。这上面说是找自己的儿子,就是找你,只要能帮着找到你,都重重酬谢。但这都是假的,当一个好心人把你送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把你勒死,那个好心人也不会得到什么酬谢,只会得到棺材钱,但那是什么棺材,一床草席子,当然,有时候这个都免了,都剁碎喂狗。也不知你惹了什么祸,半夜三更,三个年轻人打个灯笼来到我家,把我从床上拖起,我正睡得死死的,要我来张贴这鬼东西。我老婆还抱着我的脖子说了句梦话,他们就把她的手扳开了。打灯笼的把我领出来,另外两个就留在我房间里了,天知道他们会对我老婆做些什么。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老婆也习惯了,他们经常这样。到了领任务的地方,挤满了领任务的人,谁也不向谁打听,但看那阵势,就知道印了多少这鬼东西。肯定还在继续印,还在继续往外派人,直到全世界贴满,要是哪个角落被风吹掉一张,他们就会派人去补贴一张新的,不抓到你,这事是不会罢休的,你跑到天边,他们会追你到天边,你跑到九十岁,他们会追你到九十岁,就算所有知道这件事的都死光了,那些文件还会继续指引着后人做同样的事。你得罪了他们,就准备逃一辈子吧。太阳升起时,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也将贴满这鬼东西。你让一下,我要在你头上贴一张。真是要命,在这样鬼都不出来的夜里,我却要来贴这招鬼的符,而他们却钻进我老婆的被窝里。”
他从自己脚边的一只木桶里操起一把铜铲,铲起一铲面糊涂在墙上抹开,就把手上那张纸贴上去,抹平,又提起旁边的灯笼照了照,说:“你还站着干什么,快逃命去吧,别跟着我,我还不想要那棺材钱,虽然我活得连狗都不如,可是我还是想活着,活着至少还能抓抓身上的虱子,挠挠痒儿,你想想,躺在棺材里,一根蛆在脚板心里爬,却不能去挠一下,那多难受啊。哎呀,这面糊不能吃的,我刷了多少面墙了,铲子沾的泥都在里面。快跑吧,天再亮些,你就跑不掉了。我告诉你,从这条巷子一直走到城墙根下,向右——就是你抓筷子的手那边——沿着城墙根一直走,那边城墙已拆掉几处,在那里出城,远远能看见一棵大古树,朝着它走就能走到河边,向河上游去,到处都是山,躲得过,躲不过,就看你的命了。”
他穿过巷子走到城墙根下,看见城楼在左边没多远,犹豫了一下,就飞快的跑到城门口,不见他母亲,又飞快折回,沿着城墙往右去。出了城,天还未大亮,远望一切仿佛都浸在井水里,一团巨大的黑色树冠堆在田野的尽头。往前去,树一点一点的露出来,果然是棵大古树,树下有个小小的几片石板搭的土地庙,前面石板上供着几个斋粑,一堆新纸灰。他顾不得害怕,拣起一个斋粑就咬了一口,沙子在牙齿间噔的响了一下,硌得牙齿发软,也不吐出来,嚼也不嚼就直接吞下去了,随即把其余几个斋粑都拣进衣兜。
河就在树旁,水面不是很宽阔,对岸有个庙,瓦上铺着青烟。一个小和尚正站在河边往这边张望,拿根竹竿在水里划,像是在捞什么。他拣个石头扔到河里,一串气泡从水底升上来,水草随着摆动,于是又拣了个石头扔进水里,盯着摇摇摆摆冒上来的气泡看了会,然后才向上游走去。河湾一棵柳树下的石头上,整齐的摆着双很旧的布鞋,白底黑面,白底已经发黑,黑面开始泛白,两只鞋尖大脚趾处都穿了孔,鞋后跟贴在鞋底上,快踩没了。左边鞋子外侧半边鞋尖沾了一层湿泥,泥的边缘已微微有些干了。鞋子又长又大,他想穿这双鞋子的一定是像煤渣子街的单身汉吴长子那样又高又大的男人。鞋子的旁边摆着杆两拃多长的竹烟枪,烟嘴和烟锅都是铜的,黄里泛青,烟锅里还有一锅新烟。另外还有一个空洋火盒,一根没药的洋火棍。他四下里张望,宽阔而平坦的垄地没有一个人,都是丛杂的野草,对面也没有人。他拿起那根烟枪,抚摸光滑的烟杆子,端在眼前往烟嘴里瞄,托着烟杆,衔着烟嘴,学煤渣子街又留起小辫子的刘老太爷训斥那些围观他辫子的小孩子时的样子,在烟嘴上狠狠的吧一口,咬牙切齿的说,“但得一张树叶(张叔夜),扫光你们这些孽种。”但不能象刘老太爷说话时那样眼睛鼻子一齐冒烟,他未免有点遗憾。随即坐到石头上,学李屠户的样子,右脚搁在左腿上,右手肘顶在右腿膝盖上,捏着烟杆,吸上一口,偏着头说:“嗯,刘老不死的那三根癞毛,留了好多年了,还没猪鬃毛长,剃个半秃,活像个猪屁股,吹胀后,光剩尾巴根那圈毛没刨的猪屁股就是那个样子,一根花白尾巴,以后他再说拿张树叶扫光你们,你们就说拿个铁勺刨光他的。”停一下,吸了一口,提高声音说:“对,刨光他的。”装作嘴里吐出一口烟的样子,乐了起来。
他用洋火棍挖净烟锅里的烟,又把烟锅小心的在石头上磕了磕,起身慢慢的走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把鞋子也提上,向水边走去,暗绿的河水漂着零碎的树叶草屑,倒映着暗蓝的天,仿佛深得天的倒影才是它薄薄的底,水草幽幽的舞动,好像水底沉死人的长发,四围静得出奇,他不由得害怕起来,立刻离开水边。
他在河岸上找了个浅水洼洗了脚,坐在石头上,风干脚,才穿上鞋。鞋实在太大了,不跟脚,他拖着它们走仿佛拖着两只逆水船,所有的心力都在它们上面,不敢稍有松懈,否则,它们就要随流水漂走了。走到岔路口,犹豫往哪走的当儿,看到路边枯黄的茅草,就扯了一把,分作两股,都拧成麻花,每只脚连鞋子在足弓处捆了一道。他是见吴长子这样穿过。有年冬天,天气很冷,吴长子从他家门前过,脚上有只鞋子就捆了一道草,他跟他母亲打招呼,正在做针线活的她抬起头,笑着用眼睛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从矿上回来,下坡时滑了下,把只鞋子滑穿了,所以那样捆道草,好走路。她就叫他脱下来,飞快的替他缝好,很快活的看着他穿着走远。
他直起腰来,走了两步,虽然硌脚,但稳当多了,脚也暖和起来。“儿子,你知道吗?吴长子也在矿上死掉了……。”他忽然想起他母亲有次像跟他报丧似的这样说,她说话时那种难得一见的伤心神情一下子在他脑海里凸显出来,但随即远逝暗淡。他站住了,极力维持,反而立即模糊了,只剩目光还在脑海里远远望他,跟小鸡被他踩伤后临死时的眼光一样,渐渐微弱,渐渐熄灭。他不禁悲从心来,边哭边向最偏僻的那条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