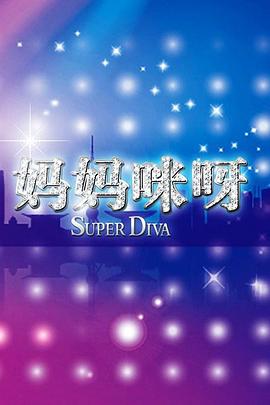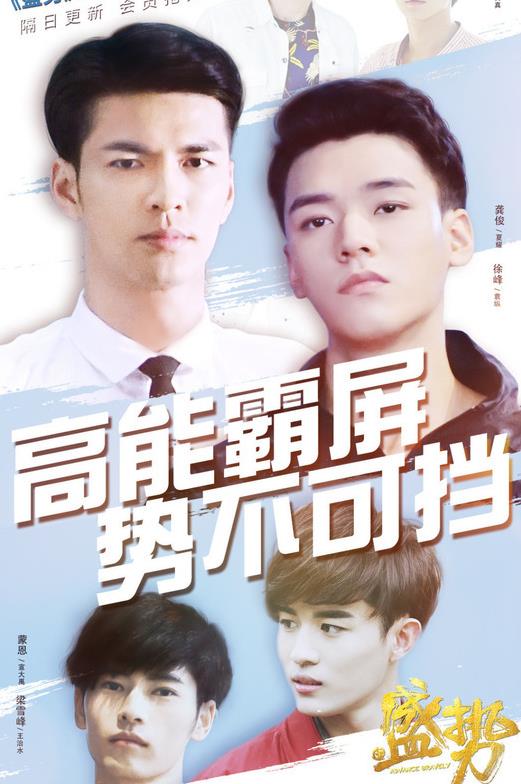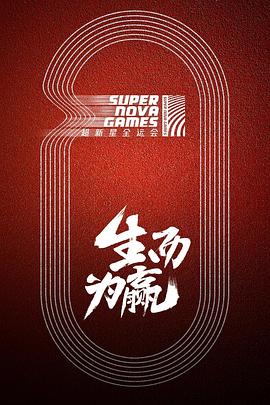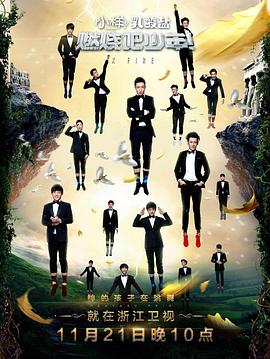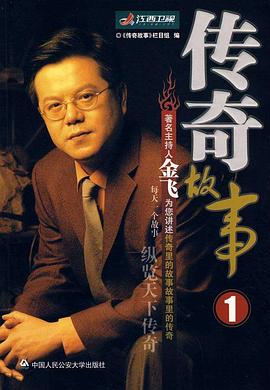剧情介绍
在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小编将每日为您带来精彩内容,希望您不要错过哦~
文|扶汐染
编辑 |扶汐染
前言:
《妈妈咪呀2》延续了前作的剧情,欧·帕克执导,演的喜剧歌舞片,该片于2018年7月20日在美国上映,曾被提名第9届好莱坞音乐传媒奖最佳奖。
讲述了苏菲为了实现母亲唐娜的梦想重新修缮装饰旅馆,并广邀自己和母亲的朋友参加盛大派对的过程,并将唐娜与三位恋人的相遇相知悉数道来。
影片,采用双线叙事、时空交错的方式演绎了不同于舞台剧的故事,既完成了续作使命,又带来令人惊喜的“前传”,将唐娜和苏菲母女的情感经历恰到好处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无论是前作还是续作,影片都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母女二人热情、乐观、积极、勇敢的精神打动了无数观众。
而在歌舞场景的语言叙事中表达这一功能是第一位的,虽然这种表达可能有时会中断叙事的发展。
但似乎所有的歌舞场景表达,都与电影试图表达出的主题和电影追求的审美倾向息息相关。
尤其在《妈妈咪呀2》这部电影中,歌舞场景作为一种叙事语言,参与到整体情节发展当中,对电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且从更深层次上看,这部电影中的歌舞场景作为一种审美语言,本身就带有着浓重的、有目的审美特质。
本文从这一视点出发,试图分析这种赋予在歌舞场景中的审美内涵,为这部电影的评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结构的建构
在音乐电影的叙事表达中,往往无法跨越歌舞场景这一关键结构的建构。
与其他类型的电影相比较,音乐电影更加注重通过音乐和有关音乐的艺术形式,展现或者表达电影文本,对于某些社会问题或者人生问题的思考。
这些富有意义的、与音乐息息相关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音乐电影独特的表现手段,而且同时也是电影所试图表达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美学观念的重要承载形式。
如果把歌舞场景,看作是音乐电影完成叙事的一种语言场域,那么这个语言场域中所表达出来的内在逻辑,和审美观点,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电影文本的基调。
而这种基调仿佛是电影叙事的先验性逻辑,构成了电影叙事的整体风格和主要特征。
在音乐电影的歌舞场景这个语言场域中,主要由歌曲和舞蹈两个方面,构成了人物对话和叙事者表达的语言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所谓的语言场域,所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表达方式,或者是在电影领域当中的镜头语言。
而是由歌舞场景中的演唱,以及人物之间的演唱关系和舞蹈,以及肢体语言关系,所形成的表达情感和审美倾向的表达方式。
一般来说,电影中的配乐有两种,一种是旋律性的,通常都是对情感发展起到烘托和暗示作用的曲调。
电影通过这些旋律的营造,建构起依靠镜头无法表达的电影情感或者环境它既是镜头语言的补充,同时也和镜头语言相呼应。
另外一种配乐则是主题性的,它贯穿电影叙事的始终,或者是在电影的高潮部分反复出现的旋律,在整体的电影文本叙事中具有一定的结构作用。
但是这两种配乐都与音乐电影中的歌舞场景在叙事层面,和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意义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换句话来说,就是在音乐电影的文本叙事过程中,歌曲和舞蹈不再是一种后景化的电影叙事的辅助结构。
而是走到前台,它不仅仅在结构上,同时也在内容上构成了电影叙事的一个部分。
这一方面说明了音乐电影的表达,是依托于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段的,也在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音乐电影中的歌舞场景与一般电影不同。
甚至是音乐电影本身存在的背景音乐之间的区别,也论证了在歌舞场景内部,所具有的突出存在于叙事背后的审美观念。
歌舞场景作为一种审美语言的建构
歌舞场景作为一种叙事语言,不仅在电影叙事文本中承担着叙事的作用,并且在叙事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创作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赋予,在歌舞场景中的审美取向。
作为一种审美语言,歌舞场景用自身的艺术特色,不断建构着《妈妈咪呀2》这部电影内在的审美世界。
从歌舞场景中的歌曲侧面来看,整部电影的演唱,都是在突出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关系,在歌曲演唱的过程中,人物之间和歌曲的风格,与内容之间形成了巧妙的互动。
比如唐娜刚刚抵达小岛发现农舍的时候,她对这个农舍未来的设想都在同一首歌曲中由女儿苏珊进行了实现。
作为被时间重塑的空间形态,唐娜和苏珊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共同理想的追求,而这种共同理想的最终实现,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众亲友的支持与帮助。
这些人都在各自的生活中,回归到苏菲和唐娜的共同理想中来,并且对这个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帮助。
从电影文本的内容上看,唐娜与苏菲的理想是重建农舍,并且将它改造成一个可以为人带来欢乐的场所,这与唐娜的人生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娜是一个追求自由、信任他人的“旅行者”,她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结识了苏菲的三位父亲。
然而在这个看似混乱的情感关系中,每一对人物之间的互动与关系都是和谐的,这是因为在文本中他们的追求,都是围绕着唐娜展开的。
而从电影中这种理想的隐喻含义来看,这座为人带来欢乐的旅馆,所象征的恰好就是,一个为人带来欢乐的庇护所,这个庇护所的建成,实际上又都依赖于很多人带来的帮助。
而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又刚好呼应了这个庇护所的主题,也就是电影对于美的判断准则,那就是对幸福的追求。
再从歌舞场景中的舞蹈侧面来看,音乐电影歌舞场景中的舞蹈动作,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舞蹈艺术的展示。
更多的是为了显示出人物关系而呈现出来的,一种肢体语言,这种肢体语言与歌曲内容一道构成了人物对话的一种方式。
然而,在《妈妈咪呀2》的歌舞场景中,肢体语言之间对于矛盾和冲突的表达几乎没有,反而是更多以共舞的相互呼应的方式,建构人物的内心世界。
比如,在电影中唐娜与山姆最终分手,两人对爱情的期待和对生活的幻想,已经渐渐破灭,电影的叙事应当迎来了矛盾相对突出、氛围相对灰暗的叙事阶段。
这时出现的歌舞场景,在歌曲的设计上曲调也相对舒缓、哀伤,但是在肢体语言上。
两个人物的动作都是相对和平的,并没有歌舞场景中出现肢体上的冲突,这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来自创作者对于美的取向,那就是对和谐、善良的真挚情感的歌颂。
这两种语言所构成的语言的场域生成了一种多角色互动的效果,虽然是类似于复调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实际的歌舞场景之中,多人物之间的价值取向却又都是十分相似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的“复调”中,并不存在着多种人物对话的争论,而是从不同角度对某一个悬置在人物、叙事,甚至创作者之上的核心意识形态的。
一再确认,这种被确认的核心观点,恰恰就是电影试图表现出来的审美态度。
《妈妈咪呀2》的人性审美观
《妈妈咪呀2》所营造出的审美世界,实际上就是在歌舞当中所展现出来叙事过程中的,通过歌曲演唱和舞蹈动作,这两个重要的艺术语言建构起来的审美逻辑。
在这个逻辑之下,叙事的走向和人物的选择,都会遵从这个审美逻辑并且逐渐自主地构建起一个审美规则以及这个规则的边界。
所谓审美规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审美倾向,但是,与审美倾向不同的是,审美规则更带有一种强制的选择意味。
也就是说,审美倾向下的文本叙事可能存在着复调,而审美倾向只是对于最终结局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
但是,审美规则不同,它对文本内叙事中的人物选择,和主要人物身上的特性起到的是决定作用,对于这些文本而言,美的边界是相对固定的,当然也是相对单一的。
在此基础上,歌舞场景作为一种审美话语,本身也是,在这种审美规则的作用之下,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固定的审美世界。
在《妈妈咪呀2》的电影叙事中,不难发现整部电影文本指向一个更加抽象的审美维度。
人物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受道德的束缚,而且超越了世俗的理性观点,走向了更加乌托邦的维度。
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或是爱情的美好,或是亲情的深沉,都不属于这部电影讨论的目标。
反而由人物情感派生出来,主要人物对于某一个选择的追求,才构成了电影文本所试图表达的内容。
比如在庆祝旅馆建成的晚会里,苏菲和唐娜的两位好友最终完成了一次演唱,在此之后,苏菲的外婆应邀前来,并且遇到了多年前的恋人。
这场歌舞前后,突出表达的不再是有局限的某一种情感,而是透过这种多情感线索的描写,来表达更为丰富的人性特征,那就是人性本善的特征。
这是这部电影最基础的情感前提,也是这部电影所构建起来的审美世界的重要准则。
而其他的审美规则都是建立在这个准则的前提之下,并且由此构成了整部电影的美学基础,也就是围绕着善良、包容等人性之美的美学世界。
结语:
新作《妈妈咪呀2》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符合了观众追求非理性、娱乐性和日常性的审美心理。
电影对女性自由之美、歌舞之美和爱之美的深切刻画,既表达了电影深远的人文关怀,又使电影充满浓烈的美学意蕴,填补了歌舞片剧情单薄经不起推敲的短板。
它是具有非凡的审美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可以说,亲情是永恒的,亲情片也自然是美国电影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种类,而大众的审美心理却是多元的、动态的。
而可以预见到的是,在不远的未来与观众见面的美国亲情片,绝大多数,也将呈现出贴合这种审美心理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