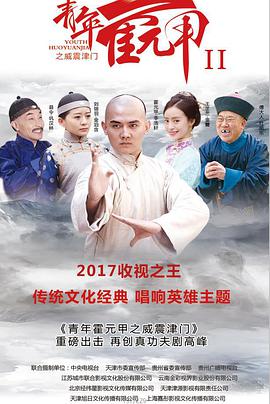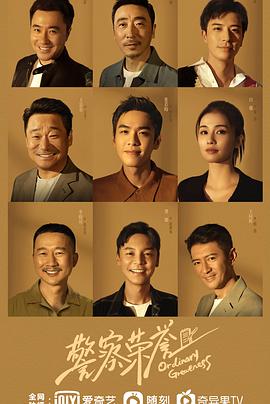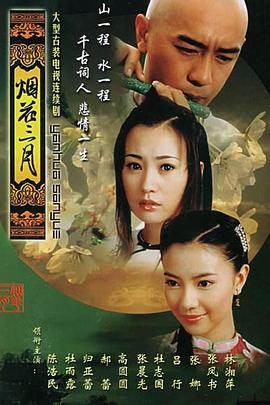剧情介绍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从天水市秦安县高铁站到石节子村,只有9公里,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但在公路没有修通之前,这9公里要用双腿走两个多小时。30年前,靳勒就是从这里走到县城上学,考上西安美院,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又成了村里的第一个教授。
2008年,已经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多年的靳勒,忽然觉得,山村不应该是艺术的荒漠,它也可以和最先锋的艺术发生关系。
此后十年,他把这个只有13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座美术馆。太多的艺术家、全国各地的美院学生,在这个村子里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留下的,是村庄里随处可见的艺术品。如今,这个山村依然贫困,但生活毕竟不一样了。
 "
" 写着“石节子美术馆”的黄土崖。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无法拒绝的家乡
进入石节子村之前,远远就能看见黄土崖壁上“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这是村民们用铲子挖成的,歪歪斜斜,有的部分已经变得模糊了,但放在这黄土高原的崖壁上,却并不突兀。
石节子是一个只有13户人家的自然村,按照行政规划,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新联村第九组,13户人家依山而建,像梯田一样,分散成五层,落差近百米,最低的一层在半山腰,下面就是数十米深的山谷,那是千万年中洪水留下的痕迹。
 "
" 石节子村依山而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2008年前,它还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而穷困的山村,这里没有水,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勉强温饱,年景不好,就要挨饿。就在去年,因为霜冻来得早,导致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幸好,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补贴了点收入。
靳勒就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上中学的时候,要去县里,那时候路还没修,每周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去县城里上学,周末又走回来。
 "
" 靳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1986年,靳勒考上西安美院雕塑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他毕业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那时候,靳勒是山沟里走出的高材生,石节子是靳勒的故乡,仅此而已。
一直到2000年,靳勒进入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开始关注当代艺术,尤其在北京这个当代艺术主要的集散地,受到老师与同行们的影响,他对艺术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我是做雕塑的,以前是学院派,觉得艺术就是阳春白雪,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但此后,我开始慢慢反思,我学到的东西,我理解的艺术,能否和村庄发生关系?”
靳勒说,“从本质上说,我无法拒绝村庄,因为我的父母都在乡村,每次回家,看到荒凉凋敝的村庄,都不由自主地想,我能做什么?”
乡村的建设者
从2000年开始,靳勒一直在兰州、北京之间来回,但只要在兰州,每周末都会回家。随着他对艺术和村庄的思考越来越多,村庄对他来说,也变得不一样了。“最开始,我是想吸收村庄的元素,把他融入到我的作品中,但这只是改变了我的作品,并没有改变村庄,所以我开始尝试把艺术搬到山村。”
 "
" 靳勒在村里的第一个作品,金箔包裹起来的树。胡建强供图
2005年,靳勒在村里创作了第一个作品,一颗金箔包裹起来的树。但村里的乡亲并不明白他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做当代艺术,离开了北京,几乎就没法儿做,没有土壤和环境,也没人理解”。但靳勒还是想尝试,哪怕格格不入。
彼时的石节子,像其他所有贫困的山村一样,沉静、死寂,只有人走,没有人来,村里仅剩的几十位村民,也都各忙各的,多少年都没有任何变化。石节子是贫困村,直到2005年,达到勉强温饱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靳勒说:“我一直在想,把山村里的生活经历、生命经验融入到艺术中,同时把艺术融入到山村里,对我、对这个山村,可能都是一个契机。”
 "
" 石节子村的村口,有个牌子写着“广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在石节子村的村口,悬崖的边上,有一个十多平方米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广场”两个字,那是村民李宝元的妻子写的,是她的作品。李宝元的妻子不识字,别人把字写在纸上,她一笔一笔照着描出来。
 "
" 当年,村民们将靳勒的雕像《鱼人》竖立到村口的小广场上。胡建强供图
在这个广场上,原本还有一个雕塑“鱼人”,是一条黑色的鱼,那是靳勒在村里做的第一个雕塑,鱼的头部是一张人脸,眼球凸出,鼻孔大张,那是靳勒把自己的脸安到鱼身上了。
后来,这个雕像几乎成了石节子村雕塑的代表作,在村里的路边草丛里,房屋的墙根里,到处都躺着这条鱼的复制品,有大有小,有黄色的、青色的,也有灰色的。
 "
" 村里都有这条鱼的复制品。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条鱼,或许可以看作是靳勒正式回归山村的象征,这一次回村和以往不同,他的身份不再只是一个探亲者,而是一个乡村的建设者。
参观德国的四个村民
用艺术建设乡村,这是靳勒的新想法,但乡村建设和艺术创作不同,创作是个人的事情,建设则是群体的改变,至少要让村民参与进来,否则建设不可能开始。
一直到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契机。那一次,有一位艺术家愿意邀请石节子村的村民到德国卡塞尔市参观。
 "
" 村民靳茂林。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于是,靳勒带着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孙保林四位村民去了德国。对于绝大部分从来没有离开过秦安县的人,德国之行或许就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那些远在德国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他们也没有任何概念。当年一起去德国的李保元说,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有人害怕,有人兴奋。在德国参观的过程,大多没有印象了,李保元只记得参观了当地的墓地,“很干净,和我们这边的不一样”。
在德国参观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欣赏油画作品的靳女女忍不住站在门口看起了大雨,一名德国记者很好奇地问他:“艺术和雨水,哪个重要?”靳女女回答说:“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靳勒说,他至今都忘不了那个瞬间,“当生存成为第一位的时候,艺术就是个奢侈品”。实际上,不止是奢侈品,村民们甚至不懂博物馆里的艺术品究竟有什么价值。同去德国的靳茂林告诉记者,“就记得那边很平,没有我们这里这么多的山”。
不过,即便村民们并不理解艺术,但德国之行,也多少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回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艺术品都是村里聊天的主要话题,村民们也愿意参与靳勒的创作了,尽管他们还是不懂。
13户人家与13个美术馆
在石节子村,想知道每户人家的户主姓名太容易了,因为他们的名字都镶在大门外的院墙上,这是靳勒的创意。
德国回来后,不久,靳勒就被村民们选为石节子村的名誉村长。靳勒自己也真正开始了他的艺术乡建之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石节子村,变成一个美术馆,13户人家,就是13个分馆,户主的名字,就是每一个分馆的名字。李保元的家,就叫“保元馆”,靳女女的家,就叫“女女馆”。靳勒家,则叫“海禄馆”,那是靳勒父亲的名字。每一家的馆名,都用细钢筋编制而成。
 "
" 孙连成的家,连成馆。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从山下盘旋而上,第一家是连成馆,这是孙连成的家,但这并不是最低的一户,最低的一户要绕路下去,叫尕成馆,是孙尕成的家。
在靳勒看来,“石节子美术馆和世界上任何美术馆都不一样”,在石节子美术馆,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包括房屋、家具、农具、废弃物,都是艺术品,甚至泥土也是艺术品。“当代艺术有特别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所有你能想象到的,都可以变成艺术。更重要的是,当代艺术关注当下,我们把村庄变成美术馆,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在这里,还有这样一群人,用这样的方式生存。”
 "
" 挂在空中的自行车。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石节子村的人们,就在这些美术馆里生活。13个美术馆,大部分都是土坯房,有的新房仅收拾过,有的还是几十年前的。不同的是,他们的屋子里、院子里,留着许多真正的作品,那是十年中来到村里的艺术家们,和村民们合作完成的创作品。
每个角落都有艺术的痕迹
2008年1月28日,应靳勒之邀,熊猫艺术家赵半狄带着他的团队来到石节子村,在这里为村民们办了一场春节晚会。保元馆的馆长李保元说,“那是村里人第一次在现实中看文艺演出,尽管没有人参与,但已经是新奇的体验了”。
此后,靳勒开始邀请更多的艺术家,到石节子村进行艺术实践,村民们也开始逐渐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当年10月,靳勒和靳女女、孙尕成等村民共同完成的作品《主人》,就被邀请到北京798展览。此后十年中,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美院学生应邀或主动来到这里,留下了无数的作品,散落在这个小山村的每一个角落里。
 "
" 石节子村一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从村口的“石节子美术馆”馆名下走过去,紧接着就是一个在悬崖上掏成的旋涡,作品的名字就叫“山旋”。那是2015年在石节子举办“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村公共艺术创作营”时,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岳琦创作的。
 "
" 旋涡和创作者岳琦。胡建强供图
岳琦解释这幅作品时表示,“这里缺水,夏天干旱而燥热,所以我在山壁上做了一个水里才会出现的旋涡,想给这个村子带来一点儿清凉的感觉。”
在岳琦看来,乡村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和这个旋涡一样,“一直在旋转,不知道转向何方,我用一种完全对立的材质,展现一种不可能的想象,寄托我对这个山村的希望”。
 "
" 靳勒头像。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样的作品,在村里到处都是,几块碎瓦片,在路边的草丛里随意地垒起来;一个新塑的佛头,放在黄土墙上挖出了的一个小洞里,还没干透,额头已经裂开了一道大缝,那是敦煌学院的学生们,在记者采访前一天刚刚做好的习作;李保元的家门口,有一座李保元自己的泥塑头像,村里总共有四座这样的头像,都是以前美院学生创作的;随便走走,两个裸女的雕像忽然出现在眼前,在这个黄土高坡上的村庄里,似乎也没人感到难为情;抬头看,一个泥塑的将军像,矗立在高处,似乎在眺望着整个山村和山谷;村子的最西头,有一座汉白玉的女性雕像,这是村里造价最高的作品,名字叫“村庄母亲”,既寓意着村庄本身,也寓意着所有村庄里养育儿女的母亲……
 "
" 村西头有一座汉白玉女性雕像,叫“村庄母亲”。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艺术家和村民的合作
十年中,石节子村举办了许多艺术活动,有电影节,摄影展、建筑研讨会,也有曼彻斯特艺术展。如今,那个名为“曼彻斯特到石节子并不远”的海报,还留在村里的一处土墙上。
耗时最长的一次活动,是2015年5月开始的“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这个计划持续了一年,由25组艺术家,和25位村民,结成对子,每一对至少要完成一个作品,不论是雕塑、摄影、绘画、还是行为艺术……
在石节子13户村民家,每一家都有一个保险箱,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放在里面,这些保险箱是“一起飞”活动中,画家毛同强和村民何蠢蠢合作的作品,叫做“寓言”。保险箱是毛同强买的,免费给每家送了一个,13户人家也同意了“交换”的条件,一年后要当众打开保险箱,看看里面放了什么。
来自北京的艺术家李颂华,则和村民靳世林合作了一个名叫“一人半身高的夜晚”的作品。在2015年8月22日夜里,李颂华脱下衣服,扛着近七十公斤的靳世林,从靳家出发,在黑夜中步行走出石节子村,沿着山路直至日出。
其实,村民们至今也不太理解这些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因为害羞与费解,不少村民甚至都不太愿意谈当初“结对创作”的故事。李保元说他并没有作品,靳茂林也是同样的回答,但实际上,在石节子村保存的资料里,李保元和雕塑家琴嘎合作了多个作品,在李保元家里的墙上,还挂着他和琴嘎的合影,而且,靳茂林也参与了一个行为艺术项目。
 "
" 村民李保元的家。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从2008年到2015年,举办了多个大型艺术实践活动,让石节子村名扬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游客、机构慕名而来,创作、参观、参与到石节子村的艺术乡建中。在村子最西面的另外一个小广场上,临着悬崖,有一座木头和玻璃建造的透明旱厕,那是德国使馆捐建的环保旱厕,以村里的厕所为原型,加以改造之后,既是公共厕所,也是一个景观,人坐在厕所里,就可以看到山下峡谷和峡谷对面的风景。
 "
" 环保旱厕。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不过,这个旱厕很少使用,门口结满了蜘蛛网。村民们自家都有厕所,不需要去公共厕所,游客们又不好意思,尽管坐在里面,外面的人其实看不到啥。
更关心雨水的靳女女走了
今年4月,北京世纪坛和798连续举办了两场“艺术乡建”的展览,展览了四个乡村“艺术乡建”的成果,石节子村就是其中一个。
在石节子村展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女女馆”,靳勒把靳女女家主屋内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北京,原样复原,实现了他“艺术即生活,要告诉人们这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的艺术初衷。
 "
" 靳勒在女女馆前。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女女没有看到这一幕,他在2017年已经去世了。他去世之后,靳勒在西安美术学院第一次把“女女馆”搬到展厅,连家门口的“女女馆”三个字,也带去了。
靳女女年轻时一直在打工,去过天水,去过兰州,盖过高楼,也盖过飞机场。去了德国以后,因为和德国记者的那一番对话,成了德国之行中最有名的村民。
但这并没有给靳女女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就如他所说,在这个贫困的山村里,雨水可能比艺术更重要。从德国回来之后,他依然是这个观点,生存才是这个山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艺术要靠后。
靳女女的家里,如今只剩年老的妻子和小儿子,大儿子已经分家单过。靳女女的妻子叫刘西花,因为年轻时重活干太多,落下了一身病,胃炎、食道炎、胆囊炎……现在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连饭都做不了,每天都要吃药,“一天三顿饭可以不吃,三顿药不吃不行”,只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门口转转。小儿子在县城打工,晚上回家,可以给母亲做饭,白天的时候,刘西花就自己随便凑合点儿。
爱画画的靳红强
在北京的展览中,几十幅如同幼儿涂鸦的画作,装裱在木框中展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叫靳红强,是石节子村里一位先天残疾的年轻人。
 "
" 靳红强和他最喜欢的马头雕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红强生下来就有病,检查过几次,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因为没钱,也就不再寻求治疗了。如今,21岁的靳红强,身高只有一米多点儿,和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腿也不方便,要拄着拐杖走路,说话声音虽然很洪亮,但多数都难以听清。
靳红强没上过学,一年级断断续续上了几次,就不愿意去了,因为疾病,他成了村里少有的留守青年,整天在村里闲逛。2008年,艺术家们来到石节子村后,靳红强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活动,从不缺席,不论是谁,都能迅速和人家打成一片,哪怕是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所有的艺术中,靳红强最喜欢画画,也学人家画,拿支笔,就能画半天。几年前,靳勒发现了靳红强的爱好,带着笔和纸,在靳红强的家里,陪着他画了一下午,此后,画画就成了他最重要的爱好。靳勒还专门帮他设计了签名,他的每幅画上,都有这个签名,有时候,签名比画还大。如今,靳红强的画已经很受欢迎,装裱后能买到600元,不少人喜欢。
 "
" 爱画画的靳红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红强的母亲和爷爷已经去世,在母亲和爷爷的葬礼上,他倔强地不肯下跪,也不肯流泪,只是呆呆地在墓前站了许久,靳勒说,“这个孩子的悲伤,在心里”。靳红强的哥哥大学毕业,在兰州工作,父亲则在附近村里打零工,家里只有他和行动不便的奶奶。
采访靳红强的时候,奶奶正在门口的地里种菜,她腿不方便,半跪半趴在地里,费劲地将土卷起来,铺上地膜,接着铲土压住,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小块地,半天还没干完。
靳红强干不了活儿,一个人在村里转悠,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问他喊的什么,他说是动画片里的台词。他喜欢动画片,喜欢画画,最想要的是一盒新的彩笔。村里所有的艺术品中,他最喜欢的是一个马头的雕塑,就在他家墙外,问他为什么喜欢,他说“大”。
两个外村人一群艺术家
在石节子村,除了留守的村民之外,还有两个长期参与艺术乡建的外村人,一个叫胡建强,一个叫冯志祥。胡建强是学美术出身的,毕业后回乡建起了乡村幼儿园,教孩子们美术。
他所在的村子,离石节子只有五里路,石节子美术馆刚刚建馆时,他就参与了,是整个石节子美术馆的副馆长,十年中,义务帮助石节子做策划、宣传、招待等工作。对他来说,石节子村是特别的,“不仅有我喜欢的艺术,还是我十多年的工作”。
冯志祥也是秦安人,是靳勒的中学同学,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汽车运用工程专业,长期从事汽车鉴定、检测工作。办美术馆时,靳勒邀请他帮忙出出主意,并且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他说,“我喜欢艺术,具体讲是喜欢画画,所以也乐于参与”。
冯志祥去石节子比较少,一般都是需要技术支持时才会去,石节子村装太阳能路灯、修理水井泵、网络调配等,都有他参与。在“一起飞”项目中,艺术家张兆宏和靳海禄合作的“家庭旅馆计划”也请他做施工技术总监,并负责水电、智能信息系统的规则安装。只是目前这一计划还在进行之中,家庭旅馆也才刚刚打好地基,远没有完成。
 "
" 刚刚打好地基的家庭旅馆计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些年来,在石节子来来往往的艺术家、美院学生、游客已经很多,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每一个人来到石节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石节子村的每一个角落都逛一遍,发现那些隐藏在墙后、草丛里、悬崖上、窑洞里的艺术品,不翻个底朝天,不算结束。“好像石节子有一种魔性,来到这里,突然就会爱上艺术”,一位来石节子进行艺术实践的学生说。
到过石节子的艺术家,都会对石节子赞赏有加,他们惊叹于石节子的艺术氛围,也怜惜村民们的穷苦和艰辛。
在李保元家门前的土崖上,有一颗巨大的“眼睛”,黄土上勾勒出眼睛的轮廓,一面反光镜和几十个酒瓶子,构成了瞳孔。
 "
" 李保元家门前有一颗巨大的“眼睛”。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个作品名为“天之眼”,是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齐浩冲的作品,胡建强说寓意是“你在看它,它也在看你”。齐浩冲则表示,“作品的灵感来自于村民们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眸”,所以他做了这么一只大眼,“眺望万物的生长与衰败,石节子的一切都在它的关注之下”。
艺术能否带不来收入
和艺术家们感动于石节子的艺术氛围不同,住在村里的村民们,对艺术则没有那么热衷,他们会支持靳勒的想法,参加村里的活动,也热情地招待来村里的人们,但另外一面,他们更多地考虑面前的生存问题。
 "
" 将军头像雕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茂林是去过德国的四个人之一,但他对石节子的艺术建设,并没有太大的期望。靳茂林早年一直在外打工,如今老了,干不动了,就在家种地,一儿一女仍在打工,他说,艺术家带来实惠,自然高兴,但这种实惠并不多,石节子仍旧很穷,“关键是没水,还要靠天吃饭,日子过得很难”。山下的峡谷里,有水流冲刷的痕迹,但那些水无助于缓解石节子的干旱, “平常没水,有就是洪水,过了就没了,留不住”。
其实,十多年中,靳勒的努力、艺术家们的支援以及国家扶贫工作的推进,确实给石节子带来了不少变化,路面硬化已经完成,路灯装上了,自来水也通了,靳勒还筹资把山下的一眼温泉引到山上,导入了每一家,这意味着,石节子的每家人,都有两个水源,一个自来水,一个温泉水。
但这种改变仍旧显得太过微小,这里的民居,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土坯房,村里甚至没有一间民宿,来村里的艺术家和学生们,大多借宿在村民家里,每天住宿和吃饭80块钱,给村民们的增收非常有限。
“靳老师是艺术家,又是村里出去的大学生,大家都很支持他,村里来的人多,大家也高兴”,李保元说,“但确实还很困难,日常生活、孩子上学……花费很大,收入却很少,艺术家来了是好事,但目前增加的收入不多,以后人多了,会好一点儿吧”。
 "
" 石节子村一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据李保元介绍,县里准备把石节子打造成一个旅游点,民居改造也提上日程了,已经请设计师设计了,当这些计划完成,或许村民的收入会更高。
“我跟靳勒说,未来石节子每家每年的收入要达到10万,但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冯志祥说,“石节子确实很穷,很落后,地方落后、人的思想也落后。老靳一直讲,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来改变现实,不光是石节子,还有秦安县,周边,落后的地方都有待改变。但总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是搞技术的,老靳也只是个艺术家,我们确实很微小,也很无力”。
记者手记
艺术和村庄,谁的梦想?
在北京见到靳勒时,他刚来布展,带着几个石节子村的村民,但村民们不太懂如何布置一个展览,一切细节,都是靳勒亲力亲为。
十多天后,展览结束,在石节子村再见靳勒,约好的时间到了,却一直没有音讯。直到在村口遇到刚从医院回来的靳勒,才知道他在北京的十多天,几乎不眠不休,布展、维护、解说、撤展,全都一力担当,回来后就病倒了。
30多年前,靳勒走出石节子的大山时,这个村里只有靳、孙、李三姓人家,一共只有4、5户。30多年后,原本的4、5户人逐渐分家,成了现在的13户,期间有过一家外来的人家,但住了不久又走了。
在中国变化最快、最剧烈的30多年中,石节子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多了一些艺术品,多了一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面孔。
是好是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艺术家们为山村的原生态而欣喜,也为山村的艺术氛围而感动。但对于村民来说,改变生存的处境,才是第一要考虑的,他们更看重的,是艺术能否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艺术本身,反倒是次要的。
靳勒介于两者之间,他是村里走出去的艺术家,想要改变山村的生存环境,但他的思维,却还是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不太擅长去考虑更多和利益相关的内容。
所以,十多年来以艺术建设乡村,石节子变了,也没变。变的是它让人惊叹的艺术氛围,人们想象中高大上的艺术品,在这里随处都是。没变的是村民们的生活,打工的还在外打工,生病的仍被疾病折磨,贫穷的也依旧贫穷……
还有一个变化,在石节子村脚下的山口,建了一个新的牌坊,上面写的不是石节子村的名字,也不是石节子美术馆,而是“神仙塔道观”五个字。这个神仙塔道观就在石节子村后面的山上,站在村里,就能看见那辉煌的建筑。据村民介绍,是上面为了发展旅游而建的,之所以建在石节子村后面,就是因为石节子这些年名声远扬,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游客。
 "
" 石节子村脚下的山口,建了一个新的牌坊,上面写着“神仙塔道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有人觉得两者格格不入,但村民们其实无所谓,如果游客能因此多一点儿,或者政府为了旅游大力改造石节子村,也未必不好。
石节子村在北京的两场展览中,中华世纪坛的展览主题叫“石节子美术馆”,798艺术区的展览主题叫“谁的梦——石节子十年文献展”。这或许是个隐喻,十年之间,艺术介入乡村,艺术改变乡村,艺术家和村民们,他们的梦想,究竟是怎样的?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